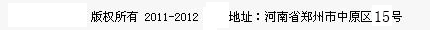深圳商报独家专访马原:带我们重返文学“黄
点击上方“文艺新青年”可以定阅哦!在今天很多人的心目中,20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各具特点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纷纭产生,文学语言叙事出现革新探索,高质量的作品成批出现,文学期刊出版大量发行……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为文学转轴的八十年代,构成了庞大杂多的声部,气势恢弘,使人怀恋。对那个迷人的时期,当年曾亲历其中的人至今念念不忘,多年来不断希望能够“重返”。对与余华、苏童、格非和洪峰并称“先锋文学5虎将”的作家马原而言,亦是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跋涉两万多千米,用时两年,与巴金、冰心、夏衍、叶延芳、柳鸣九、李文俊、史铁生、王蒙、余华、张炜、刘心武、蒋子龙、格非、王安忆、苏童、朱伟、程永新等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对话。这1可谓“文学长征”的非官方拍摄,成为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一次大规模拍摄。终究拍摄成多分钟的素材带,剪辑成份钟,分为24集的电视节目,名为《许多种声音——中国文学梦》。但是使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母带保存不善,终究只留下那次拍摄的文字版,即今春出版的由马原等著的《重返黄金时代——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随着书中文字重返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听到王蒙说:“《活动变人形》是我的全部作品里写得最痛苦的,写的时候我本身有一种在发疯的感觉”;听到史铁生说:“跟以往比,我还是认为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你可以说是收获最大的时期,乃至是最光辉的时期”;听到韩少功说:“寻根文学成文化后就深入不下去了,失误了”;听到王安忆说:“哪个潮流我都不属于”……在书中,马原与近百位文学名家大致围绕怎样开始写作生涯、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怎样看待当前的文学和文人下海和性开放、眼下最大的欲望、最喜欢的作家或书这几个主题展开交换,话题广泛,情势灵活,谈话者的回答,也因个人的性情及经历,或大段论述或寥寥数语,或严谨凝炼或幽默活泼。它既提供了那个时期文坛的各种真实声音,其中不乏对文学、文学史、社会及人生的严肃思考和剖析,也记录了30年前那些声名远播或初露头角的大家的思想情怀。诚如马原所道:做这十年的片子,使文学这个梦继续往前走,也像史铁生说的“能使文学梦继续做下去”。马原,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年生于辽宁锦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后赴西藏担负、,开始发表作品,—年任教于同济大学,现定居云南。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拉萨河女神》《拉萨生活的3种时间》《喜马拉雅古歌》《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游神》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牛鬼蛇神》等。1小说家、诗人是八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明星:浏览这本访谈录,随处可见您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绝不隐晦的迷恋和肯定。书名用“黄金时代”来描写八十年代,就是一种非常理想化、浪漫化的感觉。马原:这本书现在已是第三版。初版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版也超过十年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我一直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称为中国文学的黄金年代,我觉得比上世纪3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事实。你看大家今天熟知的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比较写实的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到比较讲求方法论的阿城、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包括80年代末90年代初延续过来的新写实主义的名家,像刘震云、方方、池莉、刘恒等,这些人其实构成了最近几十年中国小说的中流砥柱。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应当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学成果的一个盘证。我个人以为,八十年代中国最红的人,不是当下的那些小鲜肉,不是那些电影明星,那时的小说家、诗人当真是八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明星,成果可能现在说尚早。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文学历史当中究竟能占到怎样的地位,现在说或许还早。但就当时的盛况,完全可以把八十年代称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跋涉全国各地去采访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成为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拍摄。也就是说,您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意想到八十年代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类敏感是如何萌发的?马原:你说得非常对。这本书的成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就是当年《中外文学》杂志的主编张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非常了不起,是他最早给我建议。同学都叫我大马,张英当时就说:大马,你想一想,现在是一个多好的关口(这时候是年),如果说文学有时期的话,那末新时期肯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文学时期。我们说的新时期文学是从年到年,中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小说。外国在小说的内容及方法论的探索上走了1百年的历程,而我们中国只用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特别丰富的较量和争辩,也可说是争吵。由于张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同时是一个学者,对历史有比我更明晰的敏感,他认为一段历史恰好结束,趁人未走茶未凉,争取把历史的尾巴捉住。他就跟我说:大马,你无妨做着这件事,你自己又是这段历史当中的1分子,而且你和这段历史当中的主角都有很多的交集和来往,如果你捉住这个机会,把历史的尾巴捉住,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用电视讲文学断代史的特别好的范本。当时张英就有这份敏感。固然这个事情做起来会有难度,而且你在文字当中乃至都可以看出,由于这是一个电视纪录片,我们一个摄制组跋山涉水在中国跑了那么多地方,到这些作家云集的城市或所在地,可以说当时非常辛苦。而且这又触及投资。我们对这个事情比较难过的是,我们没有一点儿来自官方的投资,都是我们几个好朋友自己掏腰包。现在可能钱不是很多,大概几十万块。但是做这件事变成我一生当中几个未竟未了的遗憾,由于这个电视片终究未能以它的个性播出来。现在这个片子已不行了,只剩下文字。当时我们做了24集,每集30分钟。采访的原始母带有四千多分钟,终究剪出了分钟。其实它变成我个人的一段经历,现在更多的是记忆,带子不行了,经历本身也不重要了。重要的就变成记忆,对个人而言。
《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
2有、出版家、翻译家,还有作家、诗人:这听起来很让人忧伤,现在看不了电视成果。或说,几乎没有可能再出现这样一部比较大规模的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名家的访谈纪录片了。马原:没有,最少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你看看这本书的名单,中国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大小说家,不说一打尽,肯定有几个遗漏,但是大部分在此。更了不起的是我第一次把文学里面的特殊群落——中国的大翻译家带到这部作品中来,都是人们特别敬佩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先辈;同时里面还有一个群落是、出版家,是让文学变成公众读物的了不起的推手们。全部文学系统构成了这么1本书,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个大系统,惯常的文学主题的作品中可能主角都是作家、诗人,是这些创造性劳动的主角。但这本书里不完全是,当中有、出版家,有翻译家,同时还有作家、诗人。我两个好朋友朱伟和程永新是大师级的,他们其实在那个时期当中所处的是有一点核心,有一点关键的位置,由于他们各自在核心的国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主持或做部主任的工作。当年朱伟就是《人民文学》的部主任,程永新是《收获》的部主任。可以这么说,中国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环绕着几个伟人一般的,是大家的核心。:当您跟这近百位文学名家交谈时,有没发现大家的“八十年代”具有哪些共性?马原:首先在我采访的群落当中,我在其中肯定是比较年轻的,比如夏衍、冰心、巴金,包括比他们晚一点的汪曾祺,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敬意的。首先他们除是我的文学先辈,他们有些人的年龄就像我的爷爷辈一样,比我父亲年龄都大很多,你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和这些已书写了之前中国文学历史的伟人们面对面,这对我一个晚辈来讲应该是莫大的荣幸,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一个太好的机会,那时我也差不多四十岁了。你在四十岁的时候,虽然已接近不惑之年,可你突然发现,你在这些还活着的文学名家中,其实还是一个后生,还是一个晚辈,还是一个小伙子。但有趣的是,你和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9十多岁的冰心,还是当时6十多岁的王蒙,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比你还年轻。这些一生和文学打滚在一起的先辈,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态个个称得上都是你的精神导师,你的楷模,这也是我当年觉得特别奇特的一道风景。文学让所有的文学从业者心态特别年轻,有童心、有豪情、有感恩。:像您提到夏衍、冰心这些老前辈,我倒不觉得八十年代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由于从创作方面看,当时他们已垂垂老矣,或说上世纪的3四十年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样会更贴切一些吧。马原:你说的是作为文本的书写年龄,和作为人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是两个话题。在文学创作意义上,他们已到了生命的老年,没有那种创造力,没有年轻时候那种振聋发聩,没有那种留在历史当中的雄壮和伟力,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晚年,心态是年轻的,精神状态是年轻的,随时都有非常风趣幽默、非常睿智的闪光点。当时我们团队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比我小2十岁的小伙子,他当时就特别感慨说:天呐,送给冰心女士对联的那个人叫梁启超,这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吗?历史书里的人物怎么会跟活人在一起!我当时就挺有灵感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历史!我们来到冰心家里拍冰心,本身就是历史。但是这个老人特别轻松,特别滑稽,而且笑声特别动人。所以,我想说的是他们生命状态的年轻。他们到了9十多岁,将近一百岁,不一定要对这个社会继续贡献他们的小说,贡献他们的诗,他们可以贡献自己的生命,可以贡献他们的年龄,可以贡献他们带给同行晚辈的鼓舞。
《冈底斯的诱惑》是马原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在文坛一鸣惊人之作
3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未尝不是1席活动的盛宴:您自己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跟这些文学名家交换时,能够到达很好的默契,围绕文化话题谈笑风生,情势灵活,特别出现普通采访者较难有的细节。所以,作为八十年代文学“明星”之一的您,在采访时有没不自觉地夹杂一点精英意识?马原:没有,你刚才说“明星”,我们充其量就算是在场的一个人,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那个时期的文学人物,他们闪光不完全是明星,也不太像。我们一生不是用电脑写,是用笔写;我们一生是面对着稿子,面对着1盏聚光台灯。我们是那末有状态,一个短篇独处一周两周,一个中篇独处一个月两个月,一个长篇独处几年,我们这个职业完全没有明星的溢美。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文人,可能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对一个文人来讲,哪里有甚么精英的概念,你差不多是用今天的概念去想象我们当年的心态和情形。这些人各有各自的实力,有的人在当时其实名望不大,像迟子建在当时就是我们的小mm,很年轻,但是有非常好的状态,有非常好的潜质。迟子建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诗,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本书里她就是那种状态。:读到年您和格非、程永新在余华的寓所交换那一篇,其中的情境让我不由从心底里直呼:这跟我们想象的八十年代真无差异。你们几位进入了很私人化的文学交心,自剖各自的写作状态、浏览经验,表达写作观点,“现场”十分生动。马原:海明威不是写过一部特别着名的半纪实半虚构作品《活动的盛宴》吗?其实想一想,我们当时做的这些事情未尝不是1席活动的盛宴!真是有太多的类似之处,就是好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对文学的酷爱和探求的气味、味道特别相近。你刚才说到的那一幕是另外的“活动的盛宴”。
马原作品《纠缠》
4你说起《午夜巴黎》,伍迪·艾伦就是我:虽然近几年您也有出版新小说,但有部份读者的评价其实不高。有个比较残暴的说法是,您最好的创作存在于八十年代,所以他们心中的马原也就是活在八十年代的马原。现在的马原好像难以接受了。您听到这样的说法会伤心吗?马原:不伤心,最少他们说的还都是我啊。我当年和今天还是一样,带着酷爱一直以质疑的方式面对小说,面对文学。我觉得我1生活得特别好。我今年六十几岁了,从2十岁、三十岁、四十岁过来的时间里,我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还算能够被注意、被浏览、被记得的一些文本,那末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文人,其实心里还是很安慰,没有太大的奢望。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外来的一份荣幸,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认可、被浏览,但是对一个人享受自己的写作进程,享受能够被自己的读者喜欢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挺满足的,能够被同行们喜欢,乃至酷爱,这应该是一种可以告慰内心的状态。:自从十年前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有关“八十年代”的话题迄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八十年代在很多人心目中有着美好动人的独特地位。但是,如果带着问题意识来反思,八十年代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泡沫?马原:没有,我一直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身体力行者。对我来讲,非黑即白。有好的年代,有坏的年代。八十年代就是好的年代,今天就是坏的年代。我不想说,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好,八十年代也有八十年代的不足;现在有现在的不足,现在也有现在的好。如果让我选择,我选择八十年代,我不选择今天,就像我选择生活格局、生活方式,我会选择上古,我不选择今天,我不喜欢今天。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格局就设定在古代,设定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设定在晨钟暮鼓。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会在自己家里做一个钟楼,上面挂一口大钟,每天不面对社会,就是自己喜欢钟声在山谷当中的那种回响。所以,在我这里不是今天,之前、包括以后,你永久听不到我用两分法、辨证论。:像您小时候也曾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称为“黄金时代”一样,对三十年代有美好的想象。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有部电影叫《午夜巴黎》,该片所表达的黄金年代理论引我触感尤深:“如果你想留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你的现在,然后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时期才是你的‘黄金时代’。”我的理解是,我们都向往着过去的黄金年代,未来人可能也会向往他们想象的“黄金年代”,即我们活着的现当下。马原:虽然我没看,但刚才听你口述,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我不是叶公好龙,我真是把大家挤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大上海给丢掉了。上海的生活对我来讲,就像福克纳说过的去好莱坞送电影剧本一样,感觉就像拿一件毫无意义的破烂丢在垃圾箱里。所以,你说伍迪·艾伦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在告诉我伍迪·艾伦就是我。
马原作品《牛鬼蛇神》
:卢博林图片来源:资料图片文艺新青年:wyxinqn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公号长按
北京一次治疗白癜风要多少钱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