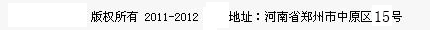汪曾祺与美食家
金实秋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汪曾祺大概是跨界最多、“帽子”最多的一位了。如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杂家、书法家、画家等等,还有一个“帽子”——美食家。尽管美食家得名较晚,但影响力不小,知名度甚高。而在这些众多的雅称中,他可能最乐于接受的就是“美食家”这顶帽子了。他去世后,诸如美食圣手、美食大师、食林盟主、风雅吃货等等光环也不由分说地带到了他的头上。一些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他关于美食文化的散文集子,从较早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五味》、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汪曾祺谈吃》,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四方食事》,青岛出版社的《家常酒菜》;到新近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寻味:汪曾祺谈吃》、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味道》、九州出版社的《旅食与文化》,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做饭》;销量不错,且有的书还一版再版,受到了亿万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诚如一家出版社的推介词中所说:
“汪曾祺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怎么个来历说的头头是道,烘托得恰到好处。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是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的人。”所以,虽然各个出版社的书名各异,选取不同;其总源也都是来自汪曾祺的美食文章;但仍然赢得图书市场,获得读者的追捧与青睐,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以及他在美食文苑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以下引述的一些美食家与汪先生的交往及其评论,则从另一角度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汪先生对王世襄之烹调艺术甚为推崇。他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盖下去了。”(见《食道旧寻》,刊年第11期《中国烹饪》)在文章结尾处,汪先生又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
那王世襄老先生忒有趣,特地就汪曾祺所讲之事及所问之题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既认乎其真地,又风趣幽默地一一作答。王老先生云:“序中说我去朋友家做菜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这是传闻之误,我从未这样干过。记得几年前听吴晓铃兄说起,梨园行某位武生,能把圆桌面像扎靠旗似的绑在背上,骑车到亲友家担任义务厨师,不知怎的,将此韵事转移到在下身上。实在不敢掠美,……。”至于“焖葱”之说,王老云:“这是言过其言,永玉夫人梅溪就精于烹调。那晚她做的南洋味的烧鸡块就隽美绝伦,至今印象犹深。永玉平日常吃夫人做的菜,自然不及偶尔尝一次我的烧葱来得新鲜,因此,他才会有此言过其实的不公允的评论。“文末,王老爷子还故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列举了糟煨冬笋、炖牛舌、油浸鲜蘑、锅塌豆腐、酿柿子椒、清蒸青鱼、海米烧大葱等七个菜,反问汪曾祺“该叫个什么菜”?随后,便坦陈其言:“‘学人菜’,我不同意。‘名士菜’,越发地不敢。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把自己做的菜称之为‘杂合菜’,“是完全符合的”。(见王世襄《忆往说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汪朗回忆说,老爷子住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爷子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大夏天,王先生上身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起身走了。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老头儿”三杂》,见朱伟《他们那一代》,刊年6月3日《重庆晚报》)
汪曾祺、王世襄这两位文人美食家,不仅没有某些旧文人的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而且有一种文人相亲,文人相惜的美德。97年三、四月间,汪曾祺曾对前来采访他的崔普权说:“你该写写王世襄先生,学者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曾推王世襄啦!”(崔善权《也馋》)王世襄也与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还说:“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陆文夫是一位与汪曾祺并美的作家、美食家,他的小说《美食家》发表后,美食家一词不仅传遍了文化界、烹饪界,甚至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遍程度。他们两人是一对知交酒友,陆文夫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作家们的活动很多,大家劫后相逢,也欢喜聚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庐山,有时在无锡,有时在苏州。凡此种场合,汪曾祺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陆文夫《酒仙汪曾祺》,见《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年版)陆文夫认为:“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同上)
汪曾祺的文化美食对年轻一代美食家颇有影响,更得到他们的敬佩和推崇。
作家陈建功也是一位美食家,尤其对涮羊肉情有独钟,别具心得。汪先生主编《知味集》,特约建功写一篇入集子。建功对此颇为自得,他风趣地说,“曾祺老对我如此错爱,我辈岂有不从之理!于是便自封“涮庐”,”还留下了“美食老饕”、“涮庐庐主”之类的美名。“有一回和曾祺老一道参加一个冷餐会,老人家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品酒,看见我来了,居然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踱将过来,指指条桌上的一瓶洋酒道:‘建功,这尝尝这酒,这酒有点味道!’这情节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仿佛一位小沙弥突然被德高望重的长老垂顾,多少豪饮者都未能得到此等殊荣。”
这一老一小“美食家”不仅交流过“吃”,还闲聊过“吃”的“工具”。一次,他们谈起烤羊肉串的钎子,陈建功说他曾用过车条,汪先生亦云:“当初我也为这钎子发一陈子愁,最后你猜怎么着?还是用的车条!”可见是英雄所见略同也!(见陈建功《老饕絮话》,刊《从实招来》,广东旅游出版社年版)
作家洪烛曾感叹地说:“我和汪曾祺同桌吃过饭,在座的宾客都把他视若一部毛边纸印刷的木刻菜谱,听其用不紧不慢的江浙腔调讲解每一道名菜的做法与典故,这比听他讲小说的做法还要有意思。好吃的不见得擅长烹调,但会做的必定好吃——汪曾祺先生两者俱佳。”(《文人菜谱》,刊《舌尖上的狂欢》,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
“不管是鉴赏食物,还是舞文弄墨”,“在这两方,我都曾拜汪曾祺为师。虽然并未举办什么公正式的拜师仪式。年,湖北的《芳草》杂志约我给汪老写一篇印象记,我就前往北京城南的汪宅,和他海阔天空聊了一个下午。一开谈文学,后来话题就转移了;因为彼此是江苏老乡,就议论起南方的饮食及其与北京风味的比较。”
“活着的文人,老一辈中如汪曾祺,是谙熟食之五味的,而且每每在文字中津津乐道,仿佛为了借助回味无穷再过把瘾,这样的老人注定要长寿的,他谈故乡的野菜,什么荠菜、马齿苋、莼菜、芦蒿、枸杞头,如数家珍,那丝丝缕缕微苦的清香仿佛逗留在唇边。……蒲黄榆的汪宅我去过两回,每回汪曾祺都是挎着菜篮送我下电梯,他顺道去自由市场。汪老的菜篮子工程,重若泰山。”
与汪老对酌,当时,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过后,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汪曾祺虽然去世了,洪烛说“可他送我的几册书中的美食散文,却经常翻读。脑海里总出现这样的画面:老人慢腾腾地把一碟碟小炒,从厨房端到客厅的圆桌上,笑眯眯地招手——“请坐吧!”
汪曾祺说自己的性格,受了老师沈从文不少的影响。而我,则受了汪曾祺的影响。我原本写诗的,自从和汪老成为忘年交之后,改写散文了。一下子就从诗化的人生转入散文化的人生。”(洪烛《汪曾祺是我写美食的师傅》《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年版)
已出版《食客笔记》、《食客游记》、《品味云南》、《辣味江湖》等书的资深食客要云说:
“这些年,在各地走,很多时候是追寻汪老足迹,为的是体味各地不同风格,让自己加入到其他人群的口味之中,体会之、理解之、喜爱之。”
美食作家曹亚瑟先生认为:“汪先生那当然是写美食文章的翘楚了。我们从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汪先生美食文章的结集就能看出他这方面文章的受欢迎程度。不敢说当代无出其右者,汪先生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符中士是一位年轻的美食家,曾应邀为两家报纸的“美食家”专栏、“食文化谈”专栏撰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食散文随笔集《吃的自由》,他自谦说是门外谈食,但识者却认为“作者丰厚的学养,幽默的调侃,独特思辩,无不令人从吃中增长知识、乐享情趣,以及对社会进行思考。”《吃的自由》付排之前,符中士慕名请汪曾祺作序,汪先生欣然命笔,于年1月作《吃的自由·序》,盛赞符中士此书“可以说是一本奇书”,还对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想法加以阐述与发挥,别具卓识。
符中士很喜欢汪先生的美食美文,在《文人菜》一文中,他列举了苏东坡、谭延闿、张大千这三位从美食家后,第四位就是说的汪曾祺。他说:“汪曾祺先生谈吃的文章,我一篇不漏地读过,但真正了解汪先生的为菜之道,还是有一次与汪先生聊了几个小时的吃。汪先生极谦虚,说他只是爱做做菜,爱琢磨如何能粗菜细作,说不上有什么大名堂。其实像汪老这样的文化修养,只要一‘爱’,只要一‘琢磨’,炒出几道好菜来,是不成问题的。汪老做的几款拿手菜,全都和他写的文章一样,不事雕琢,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韵致。”(见《吃的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他说,“我欣佩汪曾祺老,因为在我眼里,是真正的美食家”。“我平生最崇拜的美食家”“汪老走遍天下,不耻陋食、不弃新奇,孜孜不倦,死而后已。说汪老是美食大家,最是恰当。汪老不是坐在鲍翅席筵前品头论足的那种美食家,也不是陆文夫笔下的馋嘴美食家。汪老吃内蒙古的挂浆羊尾,吃太湖边的臭苋杆,吃昆明的壮羊冷片,吃塞外的莜面鱼鱼,吃侗家的牛瘪,吃维族的抓饭。吃的津津有味,各有心得。一些所谓的美食家嘴壮手软,汪老能品更能制之。美国大文豪安格尔携太太到北京,在汪老家里做客。汪老亲自下厨,几个小菜,吃的安格尔大呼痛快。临走时将剩菜打包带回北京饭店,让饭店厨师热了继续享用。何等美食,让大文豪如此倾倒?对汪老来说,不过是随手摆弄的几个家常小菜而已。”
写过《找食儿》的年轻作家人邻也是一位吃主儿,在北京的时候,曾几次去汪府去与汪老闲聊。他称汪老是“一代美文大师”,他把汪先生的美食文章读得很精,悟得也透。那几次闲聊当然少不了是要侃到美食的,至于他们一老一小聊的是什么,人邻没有说,倒是一个细节反映过他们聊得是很随便的、很开心的。在他们谈到“大煮干丝”时,人邻在回忆文章有一段别有意趣:
“这样的大煮干丝,当然是佐茶的妙品。据汪先生讲,那时,最后店家是碟子的数目收钱的。有调皮的学生,随手就将碟子抛在茶馆一边的湖水里。汪先生干过这样的事情没有?记得问过他,他只是一笑。以汪先生的性格。不会多,但一两回乘兴,还是难说的。我看着汪先生笑咪咪的样子,觉得他说起这个的时候很乐。”(《汪曾祺二则》,见人邻《找食儿》,南方日报出版社年版)
诗人石光华,是四川省美食家文化协会的文化顾问,也是一位“吃货”、“吃主儿”;他对吃笋子特有研究。他说:“笋子还有一种吃法,作成泡菜吃。泡笋子确实是真真好吃的东西,那种细脆,那种清爽,不是什么着脆的泡菜就能代替的。……泡笋子还有一个妙处,能灭坛子里的浮花……笋子进坛,有花灭花,无花保盐水,再多的浮花,七八天就全没了……当然,必须是新鲜的竹笋。”“在长宁的那一次,我把这法子说给了汪曾祺和林斤澜两位老先生,他俩都是善吃善烹的美食家,都被泡菜生花苦了半辈子。听说了笋子的这个妙处,他俩又惊又喜,叹了一声:‘啊!笋子’”石光华《我的川菜生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能得到汪老他们的赞叹,石光华引以为傲,颇为得意。
北京电视台《民俗》栏目主讲嘉宾、中华养生研究会理事崔普权曾专门去拜访过汪老,他回忆说:年“3月下旬,在作家刘绍棠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我见到了被誉为“文坛美食家”的汪曾祺先生,遂向他提出了拜访要求。汪老应允,一周后,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正是汪先生。”那天,汪老和崔普权谈了不少。谈到酒时,他告诉崔:“我现在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时候了,酒量减了一大半,该属于叶公好龙的那个范畴了吧,”崔普权说:“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天两顿酒。”(崔普权《汪曾祺:文坛上的美食家》,见《也馋》,人民日报出版社年版)
上海美食家沈嘉禄在《汪曾祺的土豆一定不很圆》中说:年,沈嘉禄“拿着魏志远写给我的地址去蒲黄榆拜访汪老。汪老的家很简朴,高层建筑,却是清水泥地。我们谈了写作,他跟我说想为汉武帝写一部小说。……再转到美食,谈到了土豆,……。”(刊年4月7日《文学报》)
陈晓卿是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他是安徽人,对汪曾祺的美食文化更是了然于心、十分钦佩。他说:“拍摄舌尖上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影响。”年9月,他特地带着摄制组和由知名作家、美食家组成的团队到高邮寻访汪曾祺的“美食”旧踪。一行人参观了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文学馆,又专程去了高邮界首镇。在这运河旁的古镇上,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华老字号”的界首陈华记茶干食品厂,浏览了汪曾祺笔下曾写过的茶干制作的工艺流程:并饱尝了一顿有维扬风味和汪氏特色的大餐——汪豆腐、红烧小杂鱼、咸菜茨菇汤、双黄蛋、煮干丝……还津津有味地吃了一碗高邮阳春面。陈晓卿说,“在众多的美食作家中,汪曾祺是我最喜爱的一位。”为了表达对汪老的崇敬和对东道主热忱的答谢,陈晓卿向古镇的领导赠送了他的美食文集《至味在人间》。《至味在人间》是广西师范大学于年出版的,在这本书的后记上,陈晓卿写道:
“我心目中最好的美食文章是汪曾祺留下的,汪先生本身是个作家,美食写得并不多,但每一篇都可以反复读,有味道。汪先生做人有士大夫的特立独行气质,写文章更能把中国文字调动到极致又不做作。最重要的,他只记述美食,不讲道理。”
台湾美食家焦桐也很喜欢汪曾祺。这位焦桐,在台湾有“教父级美食家”之称,为台湾《饮食》杂志创始人,台湾饮食文化协会理事长。他回忆说:年他到了北京,“特地去拜访汪曾祺先生。他正在书房作一幅画要送给我。吩咐在客厅稍坐,汪太太端来一盘葡萄待客,很得意地对我说:“台湾没有这种水果吧。”(见焦桐《密红葡萄》,年6月29日《深圳商报》)
焦桐告诉记者,“二十年前,我曾邀请柯灵夫妇,汪曾祺、刘心武、李锐来台访问,有一天就带他们上山泡温泉,喝茶,吃菠萝苦瓜鸡。山路上散发着疏磺味和草木气息,鸟鸣虫叫得很放肆,我和刘心武、李锐在温泉池中坦诚相见,温泉汩汩,面对好山好水,我们都沉默了,有一种震耳欲聋的寂静。(焦桐《菠萝苦瓜鸡》,年5月30日《深圳商报》)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王功走路吃蚵仔炸,吹风看海赏落日,实属生活快事,我欢喜坐在海边看蚵寮:涨潮时蚵农用以休憩、看顾蚵架的所在。海上蚵寮在夕阳余晖中,身影特别美丽。
表皮已然老化的蚵仔炸,咬开来,蹦出鲜美的牡蛎,颤动着,像被封锁的悸动的青春,忽然忆起年初访问北京,汪曾祺先生即兴作了一幅画相赠,落款用沈从文诗句:“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这几年我慢慢理解,一切虽在永恒的消逝中,犹有不会逍逝的精神和记忆,黄昏的外貌还可以激荡着青春的心灵。”(焦桐《台湾味道》,年5月31日《联合早报》网)
香港美食文化的佼佼者、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蔡澜对汪先生亦甚为推崇,他认为“自梁实秋、陆文夫和汪曾祺死后,国内就没有美食大家。”
年在故乡高邮,汪曾祺还交结了一位大厨美食家。这位美食家大名叫姜传宏,当时才三十四岁,是北海大酒店的总经理,先前也做过厨师长,是远近闻名的做维扬菜的里手行家。那年,北海大酒店正式开张,县领导诚邀汪老回乡参加大酒店开张庆典,汪老欣然应邀,并携带夫人施松卿一起回家乡。汪老夫妇就下榻在大酒店,一住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汪老对大酒店的菜肴十分满意,特别欣赏姜传宏的厨艺,尤其是对传宏研制的“姜氏葱酱肉”备加赞誉。汪老内行地说,这葱酱肉与苏州的腐乳烧肉异曲同工,高邮用的家乡的黄豆酱,则别有风味。传宏烹调的“鸭血汪豆腐”,汪老亦赞之曰:鲜嫩佳肴,连续几天都要吃它。至于小姜烧制的虎头鲨鱼汤更使汪老赞不绝口,当时就撰写了《虎头鲨歌》,并书赠时为市政协办公室主任杨杰同志。汪老在此期间,饱尝了家乡的特色菜,还在品尝之际与传宏切磋菜艺,纵论美食。他夸奖姜传宏真是个大厨,不仅为北海大酒店题写了店名,还作了《北海谣——题北海大酒店》五言长诗一首,并书写了“调鼎和羹”四个大字的横幅送给传宏。
汪曾祺的美食文化对姜传宏有很大的影响。姜传宏后来离开了北海大酒店,自己开了一家“川泓大酒店”,根据汪老的作品里涉及的美食美文,他推出了“汪氏家宴”他还把汪老笑称要申请专利的“塞肉回锅油条”改良成“油条揣斩肉”,大受食客青睐。年,川泓大酒店接待了一个台湾代表团,品尝了姜传宏的“汪氏家宴”,后说,这是他们到大陆吃到最正宗的家乡菜。姜传宏现在是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国家职业技能(中式烹调)专职评委,高邮市烹饪协会的副会长。他认为汪曾祺不仅是文章妙手,也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推广“汪氏家宴”、传承汪先生的美食文化,是同乡的本份、厨师的本份;也寄托了他对汪先生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最后,不说美食家了,改一改口味,顺手摘抄几位作家关于汪曾祺美食文化和烹饪艺术的话吧。
金庸说:“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当推汪曾祺和邓友梅。”
黄永玉在《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年版)中写道:
“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门期间,有一天他病了,我去看他,坐在他的床边,他握着我的手说:“多谢你邀我们回湘西,你看,这下就回不去了!”我说:“病好了,选一个时候,我们要认真回一次湘西,从洞庭湖或是常德、沅陵找两只木船,按你的文写过的老路子,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再走一遍,写几十年来新旧的变化,我一路给你写生插图,弄它三两个月。”
他眼睛闪着光:“那么哪个弄菜弄饭呢?”我说可以找个厨子大师傅随行。
“把曾祺叫在一起,这方面他是个里手,不要再叫别人了。”
之后,表叔的病情加重,直到逝世,随之曾祺也去世了。……如果表叔的身体得到复元,三人舟行计划能够实现,可真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别开生面的“沈从文行为艺术”了。真是可惜!年9月9日于万荷堂。)
叶倾城说:“他的书,我反反复复读过不知多少遍。今天一看,实物与他笔下所写,几乎一模一样,我有一种‘不出所料’的得意。
点这个菜,(指臭苋菜梗,笔者注)像朝圣。汪曾祺写吃食的散文,很是影响过我的饮食结构。”(见叶倾城《美食亦要文人捧》,.12.9见腾迅·大家)
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是最早发现和论述汪曾祺美食文化品位的一位学者。年,他编选的汪先生的美食散文集《五味集》在台湾出版后,在宝岛引起了较大反响。他在《五味集》的后记中说:
“恐怕在大陆文坛上还没有谁不知道汪曾祺是个品位极高的美食家。他不但熟谙中国式大菜系的特色,同时,更加追求那种不见名谱的‘野味’和家常烹饪的品尝与制作。汪氏不但品尝菜肴的品味甚高,同时还能亲自动手,烹调出耐人寻味的不同凡响的别具一格的野味家宴来。此书收入的‘美食’散文,都浸润着汪氏对烹饪艺术的独到见解和卓越的审美情趣。……从中你可以吃出文化来,吃出典故来,吃出精气神来,吃出一片人生的奇妙和灿烂来。……
吃遍天下谁能敌,汪氏品味在前头。如果说汪曾祺在烹调制作上尚不能够得上‘特级厨师’水平,但作为美食鉴别的专家,堪称‘特级大师。’”(《见《五味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年1月版)。汪曾祺对此书比较满意,他电话告诉了正在撰写《汪曾祺传》的陆建华,并赠送了一本《五味集》,题款云“建华插架。汪曾祺,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他说,此书总共有三本,手头只余一本了也。
与前几位作家所不同的是,丁帆不仅著作等身,其实也是一位美食家,只不过是“隐身”于学界罢了,即在文学评论界,也是“偶尔露峥嵘”耳。但在高校文科圈子内,丁帆的“美食家”声誉是很高的,他身上有民国教授“吃货”“食神”的流韵余风,懂吃会吃,能品能写,徐兆淮说他是一位“口中有味,心中有谱,笔下生花的美食家”,那是不错的。他现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家学会常务理事……;学术活动频繁,多方应邀受聘;顺便遍尝各地佳肴,不亦乐乎!笔者曾建议他一本美食散文集子以供世人分享,他笑而不答。我以为,或许他已成竹在胸矣。
汪先生在《知味集》后记中说:“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使中国的烹饪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正路,需要造一点舆论。此亦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而作家在这方面是可以尽一点力的;多写一点文章。”(见《作家谈吃第一集——知味集后记》,刊《汪曾祺全集》第四卷)汪先生是把美食文化当成“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来写美食美文的,并动员作家为此尽力,这不是哗众取宠或哄抬拔高,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精辟卓见。汪先生和美食家们的心血和辛劳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值得人们纪念和传承的。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本文配图和文字以及音频未注明作者的,敬请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