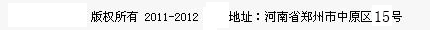北京扁平疣医院医师介绍好 http://baidianfeng.39.net/a_xcyy/210119/8604573.html这本二三十万字的小书终于赶在年12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原本就是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而作,所以无论如何不应拖过年。本书说的是深圳20世纪90年代的真实故事,无一字虚构。走过90年代而对当时社会情境已经淡忘而又无法在当今的叙事框架中找回记忆的朋友,或90年代以后才加盟深圳的朋友,不妨拨冗一读。本号明起也会选择一些章节陆续发布,既是分享,也是讨教。自序:宏阔背景下的非主流叙事辜晓进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可能也可能成为不可能。那时,侯为贵带着一个民营团队接管国有企业中兴新公司,以“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新花样,竟搞出一个风生水起的“中兴通讯”;同是国有企业的“润迅”,其“一呼天下应”的寻呼机却上了巅峰又跌落谷底,一不小心逼出个马化腾,成就了后来的“腾讯”。那时,任正非的华为一度惨淡经营,却奇迹般度过难关,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中国最富创新精神的伟大企业;“夏氏四兄弟”中最大胆的老四夏春盛,其一手创办的“黄金灯饰”,却在迅速成为“亚洲最大”之后困于三角债和资金链断裂,倒闭走人。还是那时,金陵美女杨筱妹管理的岁宝百货,开启了深圳的“大百货时代”;而规模居南山区之首的蛇口天天商业城,却在忽悠大批消费者并开出一堆空头支票后悄然关闭。一场官司尚未打完,其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已双双失联。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传媒,有的开始成熟,有的刚刚草创,有的生了又死,有的死而复生。《深圳特区报》在“小平南方讲话”后一纸风行,以卫星传版和12个外地分印点,将报纸铺向华夏四方,覆盖全国98%的市县。《深圳商报》在休刊又复刊之后,打起“政府机关报”的旗号,在不断向深圳特区报叫板的过程中快速崛起。与香港星岛日报集团合作而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中外合资日报的《深港经济时报》,在以6大张24个对开版试刊三期后,因政策突变郁郁收兵,全国各地招来的大部分新闻骨干作鸟兽散(少部分留在只能在香港注册的《深星时报》继续工作,该报后因深圳特区报兼并香港商报而停刊)。市场化媒体《深圳晚报》和未获刊号而只能随深圳特区报发行的《鹏城今版》接踵出刊,在另一个战场捉对厮杀。横空出世的深圳有线电视台,为被香港电视压抑已久的深圳电视媒体打了一剂强心针。没有“人民”二字的深圳广播电台,以“深圳事大家议”节目成为与“人民”互动最频繁的本地官方媒体。深圳期刊的“一哥”《深圳青年》因创造性的文稿拍卖而大红大紫,却又在一起官司中毁誉参半。被称为中国纪实摄影摇篮的《现代摄影》杂志,虽屡换马甲仍触礁停刊。曾因批评袁庚而为业界瞩目的《蛇口通讯报》,倒下两年后诞生了《蛇口消息报》,独存至今。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报人,职业精神焕发,竞争意识膨胀,有一些新闻理想,讲一点专业主义。特区报一小股创新势力,孤军深入后来被称为“福田中心区”、现在是高楼林立之CBD的荒芜地带,办报之余,踢球为乐。深圳商报来自各地的一些孤男寡女,下班后迟迟不愿离去,在蓝光大厦租用的办公楼里,围坐军棋盘,沉迷于“四国大战”。晚报现在的当家花旦们,那时风华正茂,靓丽如春,跟着一个精力旺盛、永远不老的精明男人,品味着创办报纸的苦辣酸甜。更多懵里懵懂的年轻书生,则蜗居莲花山、冬瓜岭两大临时安置区,过着清贫生活,写着天下大事,在泥水里趟进趟出,乐此不疲。那时的我,于年7月别南京,转佛山,经广州,到深圳,于28日晚入职深圳特区报社。一路不顺,有惊险。从南京飞佛山(为省费用走的军用机场),再转乘大巴经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广佛高速至广州火车站。下车后,为搬大巴肚里的行李,暂放下从不离身的“密码箱”。行李刚到手,同行的东南大学科研处黄处长惊呼:有人抢你密码箱!抬眼一看,一青年拿着我的密码箱已跑出50米。箱里有我的全部证件、钱钞和其他贵重物品。我请黄处长帮我看住行李,拔腿就追,跑出此生最快速度,一直追到一条小巷深处。那“烂仔”见我怒目逼近,才将箱子扔下逃窜。火车站排长队买到了站票,到达深圳罗湖火车站。下车后完全打不到的士。好不容易拦住一辆破旧小面包,却只同意载一人,我让黄处长先走。最终还是左右问人,拖着行李找到附近公交站,乘坐8路车到达报社,此时天色已晚。两天后,去广州办理从中国人民大学托运过来的行李转运(那时外地行李不能直达深圳,要从广州转),也是大费周章,还因“超期”被罚款元(相当于那时内地普通公务员三个月的工资)。买好车票,唇焦舌燥,酷热难当,在广场小摊买一片西瓜解渴。有了上次经历,为防盗贼,吃瓜时胳膊紧紧夹住小皮包,不敢大意。瓜吃完,手一摸,包虽没丢,两个裤口袋里的零钱等物已被人掏得干干净净。那时的广州火车站的秩序真实刷新我的观感。当然,那时深圳的治安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大白天,在深圳特区报社门口的深南中路公交车站旁,我太太拉着的行李箱曾被两位骑车青年公然抢走,后被我急追夺下。那时出门,没一点体力还真不行。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在深圳特区报行走多个部门,顺序是专刊部、总编室、《深港经济时报》(筹)、《鹏城今版》、经济部,做的都是编辑或管理工作(其中8年做部门主任直至总编助理),并未做过一天专职记者。但那时的深圳遍地新闻,无论是报纸需要还是职业兴趣,我都忍不住去写点什么。10年内发表的新闻和评论近千篇,在部主任中名列前茅。而且,由于这些新闻大都是“想去写”而非“奉命写”或“迎合写”,就比较注重新闻价值和读者兴趣。用现在的话说,比较“三贴近”。那时还是薄报时代。《深圳特区报》从我刚去时的每天8版(当时内地九成以上报纸还是每天4版),逐步扩大到12版、16版、20版。20版是90年代后期日常页数,曾与《广州日报》并列全国两大“厚报”。薄报流行短稿,提倡新民晚报原总编辑赵超构的办报宗旨“短些短些再短些”,要求消息字以内,一般通讯1字以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那时也写了不少“长稿”,多次占据一整版。那时海天出版社一位编辑喜欢我的这些文字,曾建议我将其编辑成书,定名《深圳故事》。但当时我整天埋头苦干,每天十多个小时用于工作,似乎抽不出时间做这“务虚”之事,一拖数载也就不了了之。10年后,广州花城出版社托朋友联系我,要将我写的乐评选编成书,也是类似的原因被我自己给拖黄了。倏忽20多年过去,不免“沉思往事立残阳”。回首看90年代那些文字,尽管那些新闻稿并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却仍觉有趣。其中一些文章看上去有点另类,有点非主流,最多也就是党报宏大叙事的拾遗补阙,却是当时社会情境的真实写照,也应当是值得保留的民间记忆。当然我也写过很多“主流”新闻,特别是年底到经济部之后。但那些新闻大都“易碎”,现在再读,有趣者不多,故本书只挑选若干篇收入。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都是历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有言,“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还说:“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而尊重历史的前提就是承认历史,包括“承认历史的真相,承认曾经的错误,承认先人的功业和成果,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书也是对深圳20世纪90年代宏大叙事的一点补充。拙著所涉内容,很多是深圳人不曾在意或早已忘却的“小”事,更是现在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俗”事。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有了不同于其他出版物的“别样”感觉。再将这些新闻发表的时代背景及后来走势(包括20多年后的补充采访)连缀成篇,突破主流叙事框架,赋旧事以新意,拾细节而成趣,仿佛20世纪90年代滚滚红尘中的一串小露珠,用以窥探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深圳民间生活,也自有其独特价值。这既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我费力完成的初衷。感谢《深圳特区报》所有为我的稿件做过“嫁衣裳”的领导、编辑和同事。感谢刘廷芳、余海波、岑志利、郑东升、薛云麾等报社摄影家慷慨提供老照片,以及深圳特区报胡冠一、罗静玲等在资料查找方面给予的可贵帮助。年12月25日于深圳爽籁居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新书自序宏阔背景下的非主流叙事
发布时间:2021-4-12 18:31:25 点击数: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