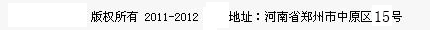早上8点30分,秋风微凉,上班的行人行色匆匆。
公司附近报刊亭早已开门迎客,窄窄的空间一前一后摆了两个冰柜,木板案台上摆放绿豆饼以及火腿肠、口香糖等零食,左侧墙面是各式香烟,只有正面墙书架上寥寥的放着几本看不出日期的杂志。
20分钟,56人路过,2人驻足,分别买了可乐和烟,买报刊的人,为零。
倘若回到十几年前,那绝不是如此冷清的光景。
回不去的童年和青春记忆拉回十几年前,报刊亭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校门口、社区旁、公交站边、绿色的小亭子里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知音》、《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是杂志货架里的常胜将军,语文老师布置的摘抄作业就靠它们来完成。最新一期的《漫客》刚刚到手没多久,就会在班里来回传阅,讨论《偷星九月天》最新一话的剧情。爱惜书本的同学甚至连杂志外的塑封纸都舍不得扔,看完后小心翼翼的装好,一本本的按日期排放,学期过后堆成了一座小山。到了放学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窝蜂的围在报刊亭的台湾热狗烤炉前,“要爆开的那根”,攥着吃早餐省下的一块钱,就是为了这一口油香油香的美味。天色未晚,还会翻一翻架子上的《啊衰》、《爆笑校园》,最简单的四格漫画总是能戳中笑点。那时,我的父亲有看报的习惯,离家不远处的报刊亭生意红火,来晚一步,最后一份《南方都市报》就会被买走。到了周末,他就会唤我帮他买份报纸回来,报纸一块钱一张,剩余的钱归我,是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的小秘密。报刊亭旁总会摆一张小桌子,社区的大爷们买份报纸坐下,吹吹水喝喝茶,从家长里短谈到国际政务,人多了还会摆出一张棋盘下象棋,这里不讲究“观棋不语真君子”,围观的人在一旁时不时的指点江山,这边说“走车走车”,另一边说“走什么车,跳马啊!”,乱糟糟的好不热闹,一直到日暮才将将散场。到了高中住校,我与报刊亭变成了一周一会。那会青春文学风头正盛,月中前,我会和老板约定好留一本《最小说》,周末来取。有时走读的同学买来一本《花火》、《瑞丽》,最是能慰藉不能带手机也没有电视的住校生们。我与同事谈起报亭,他话语间俨然像个专家——莲花二村前和百花社区里的两家报刊亭是最全的,每次放学或是周末去补习班的路上,他都要去报刊亭看看有没有新到的杂志。《掌机人sp》、《足球周刊》、《NBA特刊》……记准了每一个发刊日到报刊亭准时报到,有时售空了,报刊亭老板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就说:“都卖光啦!明天再来吧!”报刊亭最妙的地方,是它所售货物之杂,像哆啦A梦的百宝箱。小玩具、电话卡、各类游戏充值卡、放在滚筒展示架里的口香糖、电饭煲里散发着热气的茶叶蛋。这些商品有的搬进了现代化的便利店,有的则和报纸杂志一起消失在时代更迭的滚滚车轮中。有人曾说,报刊亭可能是除菜市场和博物馆外,最具特色也最能承载城市记忆的公共空间。
我深以为然,那都是回不去的童年和青春。
没落的报纸杂志或许你没有注意,曾经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报刊亭,在慢慢的从城市地图中撤离。留下来的报刊亭名存实亡,曾经摆在C位的报纸杂志在货架上落了灰,饮料零食占据了更大篇幅。有的只剩下一个空壳,转行做起了路边苍蝇馆子。我走近询问马路边的报亭有没有报纸卖,蒋姨从小角落里拿出一小叠,略带惊讶的说:“你要买报纸啊,好久没人买报纸嘞。”种类不多,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晶报、深圳商报,加起来一共29份,“现在很少人上街买报了,一个月堆这么多。”蒋姨比划着,大概一个上半身的高度,“钱都不够给邮局交管理费的。”07年到深圳,蒋姨俩夫妻开报亭开了13年,刚开始的几年,卖报纸杂志每天都有营收,加上饮料香烟热食,生意可谓红火。“现在大家都看手机,没人买报纸了,爱看报纸的老人家也是订报送到家里,不会来这里买。”和蒋姨说的情况相反,在印力中心附近的一家报刊亭,小小的亭子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拥挤又有序,而报纸小小的一叠放在角落。这里的报纸,每天都有老主顾光临,“报纸只有几个老人家会来买,有一个大叔每天都固定买一份晶报,一份商报和一份特区报。要是哪天没来,就是有事耽搁了。”“十几年前在深南大道开报刊亭,南方都市报派送过来一大叠,光收拾就能弄得满手是墨。”看起来还很年轻的老板,已经守了十几年的报刊亭。因为背靠着小区和中学,前几年报纸杂志的销量还不算难看,时尚杂志和《读者》最为畅销,“有一阵子《读者》卖的特别火,老师、学生、家长都来订。现在一本都难卖,都变成废品了。”隔着一条马路的邮政报刊亭,十几种报纸摆满了桌面,一个拎着购物袋的老伯经过买了份报纸,老板杨姨热切的和他唠了几句家常。“每天都来买报纸的,老熟人了。”得益于附近有写字楼和大商圈,人流量算中上水平,采访间隙不断有人来买水和零食,摆放整齐的报纸和杂志却鲜少有人购买,“今天卖出去两份参考消息,卖不掉的就等邮局来回收。”“报纸就几毛钱利润嘛,但是以前一天能卖四、五百份,也是很赚钱的,现在不行了,都玩手机去了。”报纸杂志不再有以前的光景,智能手机掠夺了纸质读物的城池,我问杨姨每天守店怎么打发时间,杨姨不好意思的笑笑:“也是玩手机呗”。夹缝中的报刊亭卖不出报纸,空顶着“报亭”的名头,每月的租金、管理费、房租、生活费像一座大山向报亭档主们压来。热狗、玉米、茶叶蛋这些热食和饮料一度成为了档主们的救命稻草,但也让报亭陷入成为“街边杂货铺”的尴尬境地。自17年起,深圳开始整改报刊亭,并禁止售卖热食。为了维持生计,有的档主会在上班早高峰时卖早点,到了上午9点左右便藏在桌子底下,“要是被城管发现要罚的,我们也只能偷偷卖,一年下来就挣个几万块。”占道经营、超范围经营使得报亭成为了城市规划的重点整治对象。年,深圳取缔了个无证报刊亭。一方面是城市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纸媒衰落的大势所趋,报亭夹在中间举步维艰。智能手机以一年更新好几代的速度,让人们逐渐扔掉了书本纸张,只盯着方寸间的荧光获取信息。而报刊亭,和日渐式微的纸媒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年到年间,全国共拆除了多个邮政报刊亭。一线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锐减,郑州更是在年推倒了家报刊亭,成为了第一个没有报刊亭的一线城市。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纸张转向了电子屏幕,开头不够有吸引力就会被立马滑走,一部电影太长转而看五分钟的解说,一本书字数太多转而去看高分书评,信息被切割成一个个快餐式碎片,沉浸式阅读成为了一种奢侈。曾有好友对我说“只有真的摸到实体书和报纸,我才能慢下来阅读。但工作占了大部分生活,很难有时间去图书馆,只能偶尔买书解解馋。”报刊亭就是那个在寻常巷陌里,能让人穿越到文字世界的任意门。报亭散发出的书卷气是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能匹敌的。//年,白岩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直言,“按照现在的思路,报刊亭无疑是在等死。”
他认为,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审视报刊亭,它不仅不应该消失,反而应该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深圳并不是没有行动,年,在宝安“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推行“数字化报刊亭”,让政府和报社一起统一规划新型报刊亭的建设。18年出现在深圳街头的智能报刊亭POSTORE,现在偶尔还能瞥见它的身影,但也只是零零星星。从全市范围来说,从外观装修、经营范围到售卖方式,深圳的报刊亭都迫切的需要升级转型。这是城市街头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用特地绕远路去买杂志,不用专门安排时间去图书馆,更不用忍受在手机小屏幕上看缺少“味道”的报纸。习惯纸媒的老年人也不会被城市和智能化所抛弃。报刊亭不应该消亡,而应该和深圳人一起成为这座城市的灵魂。我期待它脱胎换骨的那一天。文字闪闪摄影
丽准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注:欢迎转发至朋友圈说说你记忆中的报刊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