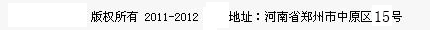当参观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的龙华(大浪)分场时,你就会发现公共艺术如何激活历史。因为浪口社区的广场最能体现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共生”,展览也在这里出发。身处广场,很容易意识到“握手楼”与虔贞女校艺展馆的区别。这种差异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矛盾。但是在“迁徙-故乡与他乡,客家历史再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展览中,矛盾是一种契机,在这里我们用公共艺术调合新旧、内外、中西、本土外地等矛盾。
虔贞学校
展览整体视觉设计所采用了靛蓝色彩和古风的细节处理,给人从容恬淡的细腻与温暖的感受。把先人与今人,历史与当代,本土与西洋,女性与文明诸多复杂而纠结的关系转换成可见、可阅、可触摸、可亲可近的呈现方式,同时又创造了一种非常后现代的审美感受。
艺术家张凯琴和雷胜的作品《游牧的故乡》,简洁又有趣,吸引着孩子们来玩耍。表面上看,《游牧的故乡》是一个形式简洁,甚至有一点童趣的作品。有些人可能认为彩色的帐篷是轻浮的。然而,当我们观察孩子们如何使用帐篷玩耍以及带孩子的老人在其中安静地聊天时,当我们看到年轻人舒适地坐在帐篷的木地板上休息时,我们恰好看到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这些帐篷将冷灰色的混凝土广场变成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就像牧民在辽阔的草原用帐篷创造一个家园一样,在浪口的广场,帐篷也让邻居们在阳光下放松,聊天,扎根。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品只是一个媒介,重要的是用艺术重新反思、发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游牧的故乡
当转向虔贞女校艺展馆时,我们发现《稻米之事》三幅一组的作品。这三幅照片的背景是年前在浪口村附近收稻的客家妇女。她们的脸部都有些模糊,但是她们的姿态让我们意识到农活的辛苦。其实,《稻米之事》再一次用公共艺术的方法来把往夕和今天缝合在一起。德国艺术家KatherinaSommer是这样阐释作品的含义:在老照片上刺绣好比人生的现实和可能性。我们都出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但是我们可以在其里面加一些自己的东西。通过时间的积累,这些东西也会让历史有所变化。在《稻米之事》中,黄色的绣花线让黑白的照片呈现出另一番味道。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一百四十多人次参与了这个作品的创造,因此它也展现出来合作和主动发挥是改善历史的前提。百年前的虔贞女校的老师也曾教导女孩刺绣,如今,小明老师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让大家共同创造了一组优美细腻的作品。
稻米之事
通过“福音堂”大门走进校园时,可以欣赏到其清新的建筑线条和宁静的气氛。在校园的古井边,驻足闭目。静下心来,就能听到香港艺术家梁美萍的作品“如尘之声”。梁女士收集破旧的瓦片,并附上敲击装置。每块瓦片都有几代人的历史,他们是隔世相传的见证者,为人挡风遮雨,承托家的精神。历史就是无数“家”的轨迹组成的来路,瓦片发出微弱而间断的沉哑之声,是浪口村、教堂和旧房的底色,如尘之声。也是向曾为这片土地奉献过的人们致敬,“他们如砖瓦,我们当铭记”。作品在不经意之中暗示的历史脚步声,如同铅锤轻敲瓦片的声音一样,人只能感知逝者如斯,却没有办法探囊取物占有时间。
如尘之声
在参观过程中,观众得以进一步解了巴色差会的历史,传教士在客家医院,和这些瑞士人在浪口一百年的奉献精神。展览的亮点之一是王艳霞女士策划的《百年相望:虔贞收藏国际交流展》,年以后,这些绘画和茶杯、客家语言课本和刺绣等日常用品都陆续从客家地区“迁徙”到欧洲去,而今大半个世纪后它们又回到了“故乡”,在玻璃柜中的每件文物带着逝水流年的回忆和家国变迁的悲欣。王女士曾经寻访过几十位随父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后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出生在广东深圳、梅州、河源等地,年前后随父母回到原籍,现在生活在瑞士或德国。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之子”,在这些“中国之子”的内心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视魂牵梦绕的广东新安县(现深圳)、梅县、河源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听这些老人家在精心录制的视频里交谈和介绍,你会觉得除了一副瑞士或德国人的面孔之外,他们几乎就是中国人,就是客家人。他们家中的陈设、琳琅满目的收藏,他们的谈吐气质,着装打扮,甚至偶尔吐出的一句客家“乡音”,都透着一种客家人特有的质朴和亲切。这些文物不只是传家宝,更是历史的痕迹,它们让我们反思“迁徙”最深的意义。来来往往的人类能留下什么?
收藏展品
收藏展现场
目前,策展团队正在和艺术家合作进行学校壁画创作,主题是“毕竟乡愁都是梦,如何再励以传灯?”壁画由两副画面构成,一幅根据巴色差会档案馆的照片,展现了百年前瑞士传教士和女教师在虔贞用现代教育的理念对客家女孩进行启蒙教学的场景;一幅表现了浪口的孩子今天在同一个空间通过公益艺术课程培养面对未来的创新能力。联系两副画面的是作为画面背景的虔贞学校,历史照片中的虔贞女校主楼和现今修复后的虔贞女校艺展馆。它不仅是一座文物建筑,更是时代的见证者,是联系历史与今天的珍贵线索。
毕竟乡愁都是梦,如何再励以传灯?
壁画所处位置
当离开浪口社区的广场时,会注意到大榕树上悬挂的艺术家方辉创作的装置《百年回声》。站在村口的大树,教堂与学校边上,不禁令人想起一百年前来自西方老师和一群客家孩子教学的场景。英文的彩色字母和汉字的笔画、部首打散和并置在一起,如果实、如根须,因缘际会、生生不息。
百年回声
“迁徙-故乡与他乡”展览在嘈杂忙乱的周边环境中安静的近乎腼腆,却悠扬如同空谷中飘来的山歌。它提示观众勿忘眼前一切熏天的短暂,而谨记内心的坚守往往历久而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