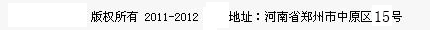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
选读四于无声处听惊雷
历史环节中,每一次突兀而至的轰动,看似无迹可寻,其实早已酝酿多时,等待着水到渠成的那一刻。一九七八年五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点燃一根导火索,引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场思想大碰撞,后被史家称作“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如果稍加梳理,便不难看出,这一场堪称石破天惊的观念交锋,早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已经埋下伏笔,随着时间推移而显现。时代转折之际的冲突与博弈,无法避免。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沿袭“文革”时期惯例,仍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所提的两个文件,一个多月前公开发表: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所做报告《论十大关系》,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经过修订后,选择在毛泽东诞辰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发表。两天后,十二月二十八日,华国锋的讲话公开发表。这篇社论经华国锋批示同意而发表,社论的最后一段,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起草者和同意发表社论的华国锋,恐怕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表述和强调,使自己一下子置身于极为尴尬和举步维艰的困境之中。首当其冲者,莫过于邓小平的复出。因为,不到一年前的清明时节,罢免邓小平的所有职务,经过毛泽东的同意,自然可以看做是他的决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二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现实情形下,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无情地摆在华国锋面前,这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的“tiananmen事件”。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强调邓小平为“后台”,从而导致他的下台。如今,走进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的复出几乎不可阻挡,可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却使华国锋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要打开属于自己的局面,谈何容易。
社论发表一个月后,三月十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三月十四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邓小平的复出与“tiananmen事件”的定性等问题,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难以越过的话题。《邓小平年谱》记载如下:
十四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tiananmen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tiananmen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邓小平年谱》,上册,一五六页)
字里行间,不难读出内心纠结处。
几个月后,邓小平显赫复出,属于他的新局面渐趋明朗。尽管如此,“tiananmen事件”平反与否,仍然悬而未决,走进一九七八年,依旧困扰中国。困扰中,政治博弈与思想冲突,从高层到民间,不可逆转地上演了。
一年一度“五一节”,如期到来。正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学习戏剧的宗福先,养病之余,走进新华书店。此时,“文革”期间成为禁书的一些文学名著,重新出版,引发购买热潮,宗福先与许多读者一样,早早站在书店门口排队,急切地与喜爱的书相逢。他回忆说,那一天,他买了两本书:一本《曹禺选集》,一本《易卜生戏剧四种》。之前他先后看过曹禺的《雷雨》和《原野》。重读《雷雨》,与第一次读易卜生《玩偶之家》,他说自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震撼!震撼带来创作的冲动,一直埋在心底的愿望,终于找到了实现的可能。
《于无声处》!一部以“tiananmen事件”为背景的话剧,应运而生。剧名源自鲁迅的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九七八年,一声惊雷,撼动中国。
将近四十年后,《深圳商报》记者楼承震,听宗福先讲述与之相关的故事:
年4月6日,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向他讲述了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一切,给他念天安门诗抄,建议他:“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但是,是暴露所有人嘴脸的时候,你把它记下来,以后肯定会派用场。”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宣布tiananmen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这正是当头一盆凉水。那个时候他看着街上走过的人都默默无声,心想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怎么那么好,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居然还忍着,真的觉得心里很悲哀。……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穿梭在欢庆的人群中,宗福先的脑海里跳出“人民永远不会沉默!”这句话,这也就是《于无声处》的主题。但他并没有马上动手,素材一直盘旋在他脑中。年3月,他大病复发住院,5月出院后,他不顾身体虚弱,一边用喷雾器往嘴里喷药止喘,一边写作,整整三个星期,写出了剧本。
(《深圳商报》,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当宗福先在上海埋头于《于无声处》创作之际,“tiananmen”的发生地北京,一个与之相互呼应的场景出现了。六月八日,全国政协文化组的一次会议在政协礼堂举行,主持会议的是组长周扬,“文革”期间他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会议开始,新当选的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社记者余焕椿,第一个要求发言。祝华新采访诸多当事人,在《政治漩涡中的人民日报》一书中,这样描述现场情景:
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逾四十年的汪东林,至今还记得余焕椿当时“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开口:
“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年tiananmen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tiananmen事件彻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年tiananmen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
余焕椿把“四人帮”插手tiananmen事件的定性、内参和公开报道的卑劣做法,连同他们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一一道来。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把很多别的界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会场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没有位子就站着听。
最后,余焕椿清清嗓子,有些激动,但更显得郑重,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发言:
“有人说tiananmen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迟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主持会议的组长、副组长没来得及表态,会场上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政治漩涡中的人民日报》,一七三一七四页)
这一次,《人民日报》走在呼吁平反“tiananmen事件”的前列。其实,早在清明节期间,“tiananmen事件”两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曾编选一个天安门诗抄的专版,但被汪东兴扣下,未能见报。这一次,在正式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余焕椿发出振聋发聩的一声惊雷。
在上海,宗福先的创作十分顺利,《于无声处》不到一个月杀青,他把剧本送给上海工人文化宫的话剧导演苏乐慈。这位“文革”期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女导演,深为剧本而感动,当即决定排演。短短几个月里,《于无声处》的公演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重要文艺事件。宗福先回忆当年情形:
宗福先把剧本送到文化宫导演苏乐慈的手中,她二话没说,决定排演。年9月22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开始公演,一角钱一张票,没想到过两天门口售票处就开始排队了。第四天上海人艺黄佐临院长就来看戏,他回到院里,要人艺所有的人都去看这个戏。接着袁雪芬、吴强、茹志鹃、邵滨孙……上海文艺界的许多前辈都来了。《文汇报》跑群众文艺的记者周玉明敏感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她写了媒体的第一篇通讯报道《于无声处听惊雷》,并把总编辑马达同志等领导都请去看戏。马达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新闻界老前辈,顶住压力,每天用一个版,连续三天刊登剧本。要知道那时的《文汇报》虽发行多万份但每天只有四个版,而tiananmen事件在北京还是个犯忌的话题啊。这几天的报纸加印几次都一抢而空。美联社立即向全世界播报了这个消息。如今深圳资深媒体人胡洪侠就精心收藏着这几张报纸,他清楚地记得,作者署名前还标有“上海热处理厂工人”这几个字。
(《深圳商报》,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于无声处》公演时,正逢第二个学期开学,我们班集体组织前去观看,第一次走进位于人民广场旁边西藏中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复旦大学历来有话剧传统。大学毕业我到北京工作后,与凤子女士来往颇多,她一九三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是复旦话剧团明星。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名剧首次公演时,都是她扮演剧中女主角,也因此而享有盛誉。一九七八年我们入学后,复旦大学先后成立舞蹈队、话剧队等。我们班的颜海平,入学前是上海杨浦区文化宫的话剧演员,她进了话剧队。话剧队在学校礼堂公演的第一部话剧,就是《于无声处》,女主角何芸的扮演者正是颜海平。之后,颜海平创作话剧《秦王李世民》,一炮打响。一九八二年,颜海平荣获全国戏剧文学奖,应邀进京领奖。此时,我已在《北京晚报》当记者,前去采访发奖大会,为颜海平颁奖的是复旦前辈凤子,可谓一段佳话。我也第一次采访同学,写了一篇人物专访在晚报发表。
回到一九七八年。《于无声处》引发轰动,直接推动“tiananmen事件”的平反进程,高层之间的博弈,也因这部话剧的传播而成为举国上下的焦点话题。于是,话剧《于无声处》调至北京公演,与高层会议的争论、呼吁,一时间形成合力,不可逆转地改变历史进程,身处人生顶峰的华国锋,渐次由盛及衰。
转折之际,两个文坛前辈,巴金、曹禺,也走到了历史前台。
《于无声处》剧组赴京演出之前,宗福先在上海作协谈到,要是这次到北京能见到曹禺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与巴金熟悉的《上海文艺》编辑彭新琪,当即将之告知巴金。几天后,宗福先即将启程北京之时,彭新琪为宗福先送来巴金的一个信封,正是巴金写给曹禺(万家宝)的举荐信:
家宝:
介绍宗福先同志来看你,他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他喜欢你的作品,看来他对你的作品还下过功夫。你同他谈,对他会有帮助。
祝
好!
巴金
十一月六日
巴金致曹禺信
人在北京的曹禺,埋头阅读《于无声处》的剧本,未等北京公演,他已写好剧评,题为《一声惊雷——赞话剧〈于无声处〉》,发表于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在宗福先同志来京之前,我读完了他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我衷心地祝贺作者,这位勇敢的青年人,我的年轻的老师。
……《于无声处》,正是写了一九七六年的中国人民与“四人帮”的搏斗。以tiananmen事件为背景,集中在两个家庭,集中在一个场景,集中在一天之内。情节紧凑,发展急剧,引人入胜。《于无声处》这个名字也起得好。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具有特殊意义。头版头条发表重要新闻:《中共北京市委宣布tiananmen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头版下方,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评论很长,头版转三版,与曹禺的剧评一起,占了一整版。同天晚上,来自上海的《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一年多的政治博弈的僵持局面,在这一天被打破,历史的天平从此向邓小平倾斜。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11月18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tiananmen事件彻底平反了。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邓小平时代》,二三七页)
《于无声处》北京首演之日,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年谱》这样记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作用,以及会议的议程变化:
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开始后,陈云在分组会议上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要肯定tiananmen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等等。会议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二十五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tiananmen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
(《邓小平年谱》,上册,四三一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写到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
由于会议的内容大大超出原定的议题,会期也超出原定的时间。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他宣布,会后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一〇五八页)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八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十二月二十日闭幕。《邓小平年谱》这样记载邓小平阅改华国锋闭幕式讲话稿的一个细节:
12月22日阅改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修改的地方为:在“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既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又要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工作,不要挫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一段话中的“既要”之后,加“作适当的处理”;同时将“不要挫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改为“在工作中继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邓小平年谱》,上册,四五七页)
毋容置疑,连续举行的两个重要会议,恰是华国锋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两年匆匆,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写到当时世界注意到的这一明显变化: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早在11月23日,即华国锋11月25日讲话的前两天,香港记者就向到访的美国专栏作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Novak)说,“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他现在掌管着中国的集权政府”。
(《邓小平时代》,二四六页)
《时代》版式对邓小平与华国锋照片的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仅十天,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敏感的《时代》用下面的表述,谈及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关系和合作方式:
邓以一种小心翼翼、相互补充的方式与华合作。华、邓联手,颇有些类似于毛与周恩来之间的作用发挥和个人关系的模式,周曾是邓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过,毛是一个预言家,而华只是传承毛的教条亦步亦趋,邓是一个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毫无疑问,邓与华之间,存在着性格差异,就像还存在着思想矛盾一样。譬如,华同意第三次罢免邓,现在看来又热衷于四个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华可能表面上担任主席,邓则实际上是指挥者。
新就任的教皇保罗二世和世界诞生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华与邓各自作用得到充分互补的情况下,如何在毛时代神圣而混乱的过去与未来的裂缝上搭建一座桥梁,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华的擢升完全仰赖于毛,他在回忆和讲话中充满这种荣耀:“政治是统帅,是一切事物的灵魂,如果不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将一事无成。”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华阐述毛的思想时,邓反驳说:“有些人天天只讲毛泽东思想,却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李辉注:此话出自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应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办法。”)
(《时代》,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于无声处听惊雷。被傅高义称作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正式启程。
五“新的长征”
一九七九年元旦,适逢《时代》新年第一期出版之日,按照惯例,需要评选一九七八年世界年度人物。这一次,《时代》评选在中国党内排名第三的邓小平为年度人物。
《时代》列举一九七八年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卡特促进以色列与埃及和解;波兰主教第一次成为梵蒂冈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叙利亚军队攻打黎巴嫩;柬埔寨与越南爆发冲突,越南入侵柬埔寨;意大利红色旅三月九日绑架前总理莫罗,五十四天之后,于五月十三日将之枪杀,莫罗身中八枪,却无一枪打中心脏,尸体放在罗马街头的汽车后厢;七月二十五日,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LouiseBrown(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但是,《时代》认为,“所有这些事件,均无法与中国决定融入世界各国的意义相比”。
此话不错。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在封闭多年之后,大踏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呢?在年度封面人物的报道一文前面,《时代》特意摘录拿破仑一句名言作为题记:“中国?一只睡着的狮子。就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将改变这个世界。”显然,其潜台词是在告诉世界,一个开始融入世界的中国,将是一个醒来的中国。《时代》所言非虚。一九七八——二〇一五,不到四十年时间,融入世界的中国已与过去大大不同。世界与中国,一切已超出人们当时的预想,一切仍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根据中国当时的宣传术语,《时代》将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冠以“新的长征”予以表述:
这一计划恢弘、大胆,堪称史上独一无二。推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十亿人民,在二十世纪的最后阶段,突然改变行程,迅速摆脱孤立状态,融入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的生活,这会不会成为史无前例之举呢?受排外情绪的冲动和封闭的毛主义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已久,一九七八年开始走向世界的大跃进,即北京宣传机构所称的“新的长征”。
在毛泽东的灾难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落后的经济日趋贫困,活力消耗殆尽,现在,他们希望在二〇〇〇年达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或许难以实现目标,或许能如期实现,不管怎样,这一启程,已呈现一个国家雄心勃勃的无比壮观的景象。
……
邓的现代化蓝图,是一九七五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医院之外的地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一年后他因患癌症逝世),周描述规划,到一九八〇年使中国的农业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一部分,这将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只需要二十年或更多时间,成为一个开始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报告(以及四个现代化口号)如今被广泛认为已成为邓小平的事业。这位个子矮小的政坛幸存者,如胡桃一样坚硬,不屈不饶,也曾受到周的保护。
……
这一战役,使世界最古老而延续至今的文明,按照日程表走进二十一世纪——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毛名义上的接班人五十七岁的华国锋,而是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虽然他在北京的政治局中只排名第三(在华以及八十高龄的委员长叶剑英元帅之后),邓实际上在中国被誉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设计师——努力同时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正因为他制定的这一巨大计划,将这个国家融进现代世界,邓小平(发音为dungsheowping)被选为一九七八年的年度人物。
(《时代》,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时代》年度人物邓小平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邓小平又一次在一月一日《时代》封面上亮相,距他一九七六年一月成为封面人物正好整整三年。
封面设计为一幅彩色肖像画。邓小平黑发间略有白发,面对前方,神情沉着,目光镇静而有力量。肖像背后,映衬一幅中国古代山水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时代》封面人物美国总统卡特
群山峻岭,云雾缭绕。不知可否理解为,古老的中国,在封闭多年之后,在这位封面人物的带领下,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行程。
关于邓小平的封面说明,相当简洁:
TengHsiao-p’ing
VisionsofaNewChina
Visions有多种含义,如视觉、美景、想象力、幻象等,在这里,将之理解为“想象力”较为合适。对于刚从“文革”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想象力。邓小平说过的两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不妨视为对这种“想象力”的印证。
复出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成为《时代》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