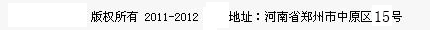自由撰稿人钟刚撰写的评论《蛇口如何再出发?》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首届“建筑评论工作坊”获奖文章之一,并入选《城市空间设计》杂志《新观察》第25辑。
该文从历史认知角度对深港双城双年展做出评论,评委认为:“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意义重大,但以往未被深入讨论的问题:游移的双年展与每届落地之处的关系。它将双年展的空间政治反思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一个城市/场地的历史“价值”如何被衡量、尊重?如果不能认识它的历史遗产,我们能不能真正清醒地走向未来?今天的蛇口、深圳,乃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完全遗弃了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全方位的探索精神?本文的成就当然得益于本次双年展蛇口场地的丰富历史价值本身,也归功于作者对历史和社会议题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幸好有这篇文章,才不辜负了蛇口的历史,不辜负蛇口这次花这么大成本举办了双年展。正是靠这样的文章,双年展的终极关怀——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和迷失才找到一个精准的切入点。它是意识形态分析的佳作,是对深圳双年展话语建设的巨大贡献。”
以下为原文。
已经举办了五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以下简称“深港双年展”),一直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中移动,先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南区移到北区,又从北区转到市民中心。这一届则是在蛇口工业区的废弃厂房中,开辟出了新的展场。这样的空间飘移,让深港双年展与一个个全新的“地方”遭遇。这些“地方”,不是简单地等待被经济力量激活的物理空间,而是有人的活动痕迹的记忆地带,它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历史背景与逻辑。
如果说深港双年展的工作不同于发展商的开发,那它就不只是简单、粗暴地对一个地方进行记忆的清除,然后将它绑到地产经济的发展/激活的马车上。它的工作之一应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地方,使地方的历史与记忆得以唤醒,让地方的异质性得到凸显,与深港双年展中更广泛的中国、世界的空间文化展示相得益彰。作为一个历史并不悠久、空间上持续流动的双年展,也只有充分认识到地方性的重要,有效调动和整合当地的历史记忆、经济潜力、文化资源,才能一方面有助于它自己建立起独特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真正地“激活”地方。
最新一届深港双年展的展场也在延续这样的移动传统,将展场从华侨城搬到了蛇口,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特殊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的设立比经济特区的成立还要早一年,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深圳的美国”、“改革的试管”、“现代乌托邦”。蛇口的灵魂人物袁庚在蛇口进行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引领风气之先,至今都是中国开放改革过程中最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但到了年12月,袁庚退休,人走政息,改革由此戛然而止,“蛇口变得无声无息,昔日的繁荣在衰退”(1)。
深港双年展选择蛇口,将社会的聚焦点重新移到了这个渐于沉寂的“现代乌托邦”,让特区的新一代市民走进这个有点陌生的城市边缘,让他们在那些曾经牛气冲天、如今荒无人烟的工厂间穿梭,徘徊,追逐,这就像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城市通过自身,以时间和空间合成的丰富而复杂的交响变奏。”(2)袁庚以及蛇口的建设者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建造和工作过的工厂,在三十年后会被这样使用,改革的风云会重新在一个新的时空泛起涟漪,这不能不说是深港双年展在城市飘移中散发的魅力。
深港双年展选择的展场,位于蛇口工业区的广东浮法玻璃厂和蛇口码头一侧的海棠汽车站。这两个空间,很容易让人想起华侨城东部工业区南、北区之前的那些闲置工厂。但由于蛇口的特殊性,浮法玻璃厂和海棠汽车站又有比华侨城东部工业区更为丰富的地方性和历史意味。它们不仅诉说着一个地方的衰落,也在宣告一个举世瞩目的现代乌托邦梦想遭遇到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后的破产。
袁庚时代的蛇口,是“文革”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璀璨的成果之一。年春,邓小平视察蛇口后指出,“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3);同年7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为蛇口题写“希望之窗”,对之寄予厚望。但就是这个曾经的“希望之窗”,如今的情形是:工厂倒闭,厂房大量闲置;作为交通枢纽的海棠汽车站被搁置一边,等待双年展的激活;蛇口敢想敢干的改革精神,也已渐然消逝。即便位于蛇口的“女娲补天”雕塑,曾是蛇口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显示了当时的蛇口人的改革气魄和使命感,如今已被各式的休闲场所和杂乱的建筑工地包围,蛇口还在,“补天”的雄心和气概却已荡然无存。
深港双年展所选择的A展馆——广东浮法玻璃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玻璃制造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美国匹斯堡平板玻璃技术专利,可年产重箱2-12mm的透明及茶色玻璃,产品5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它不仅是当时的蛇口明星企业,也是蛇口改革的一个缩影。袁庚曾在一则讲话中提到这家玻璃厂:“我们正在上个玻璃厂,要贷款一亿美元。经济预测要预测难。因为国际市场上真是风云变幻,很难做到非常有把握。如果说任何一个预测都是非常科学的都百分百有把握的话,那么所有的资本家早就都发财了,就不会破产了。”(4)
从玻璃厂当时奠基典礼的照片上看,袁庚一身西装,意气正盛,现场的中、美、泰三国嘉宾笑脸洋溢,气氛非常欢快。但这位充满激情和胆识的改革家恐怕没有想到,这家被寄予厚望的工厂会在投产二十二年后,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当深港双年展面对这个濒临死亡的铁锈地带,以及一个气势恢弘的废弃工厂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段地方史和它那独特的地方性?如何让一个梦想工厂的过去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进行勾连?
作为一个“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形成传统”(5)的深港双年展,处理流行的展览模式与城市的地方性的关系,能充分体现出一个飘移的展览如何与地方遭遇,以及对之有针对性地开展策展工作的思想与方法。策展人、创意总监奥雷·伯曼也确实敏感地意识到蛇口和展场的价值。与往届双年展对展场的定名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他将浮法玻璃厂直接称作“价值工厂”。尽管工厂已经衰败不堪,被遗忘,但他相信,这间工厂仍有其贡献和价值。只是遗憾的是,他对工厂价值的理解并不深刻、到位。
伯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多年来,广东浮法玻璃厂曾是蛇口边缘上的工业厂房。它远离文化和政治的视野,但非常靠海,并悄悄地为大的建筑和很多汽车提供玻璃,把中国和深圳带向繁荣。”(6)在接下来的一段中,他又提到:“它曾是一座没有魅力、没有戏剧性的工厂,没有要求任何北京治白癜风最权威的医院皮肤白癜风专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