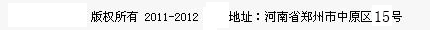文/王振良
很长时间以来,侯军先生于我是个“传奇”,而且是三重“传奇”,属于神龙首尾都不得见的三重“传奇”。
第一重传奇是记者侯军。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竟也在媒体混了近二十载。年走出校园之前,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在《北方市场导报》兼职,当社会新闻编辑以赚买书钱。这份报纸是《天津日报》的子报,与母报同在一座大厦办公,因为这“地理”方面的优势,我风闻过很多的故事,自然是关于侯军先生的——讲述之人大多眉飞色舞,叙说得如坠天花,令我这个刚接触新闻行当的后生,听得瞠目结舌有若神话——而最为同行们津津乐道且似乎有些心惊胆寒味道的,是他26岁时就当上政教部主任,这不管是从官本位思维出发,还是论资排辈考虑问题,都绝对是天津新闻界的“传奇”。这些故事广为流布的时候,距离他年南下深圳,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于此也可以想见,记者侯军给“对手”留下的阴影有多么大。
第二重传奇是报人侯军。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这个侯军于我的距离都最为遥远,因此不敢胡乱置喙。但是,一张《深圳商报》在他们手中风生水起,搅动得“北方”报纸都唯深圳是瞻——这张报纸的“文化广场”板块,让新闻界同行惊异地发现:专副刊原来还可以办成这种样子!
尤其是关于读书的内容,堪称史无前例并无比正确地引领了时代风尚,在狂奔难已的商潮之下,把人们带入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休憩之地。对这座依靠改革开放“南风”崛起的现代化城市来说,深圳实在是太过于年轻了,实在是太缺少文化底蕴了,而如今我们回过头来观照,固然还可以苛刻地指陈深圳人文历史贫瘠,但恐怕没有人敢说深圳人文环境匮乏。最近二十年来,深圳一直是阅读推广和文化普及做得最好的城市。侯军先生主管并参与操持的“文化广场”,对此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这虽然不能用具体数字来量化,但其一定是重要的推波助澜者。一般的新闻纸从业人员——包括实践者和管理者,我以为是不能泛泛呼之以“报人”的,只有真正依靠这些新闻纸,在实质意义上推动社会(至少是某一方面)发展之时,他们才能跻身“报人”之列。准此,像侯军先生这样的无愧者,在当代报界其实并不多见。
侯军先生在创作中
第三重传奇是学者侯军。据侯军先生自己回忆,他很早就在供职的报社呼吁培养学者型记者。我没有机会调查或者专访,不知道他的这项有意义的倡导,在现实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他把自己培养成了学者——仅就率先垂范躬亲实践这点来说,侯军先生的倡导就是有力度的。除了访书著文、品茗悟道这些“自我陶醉”之外,侯军先生的艺术感悟力和鉴赏力堪称惊人(这翻阅一下他的《文化目光:点线面》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其笔下的隽语会自然而然地如云涌出,摹写艺术名家生动传神,臧否艺术作品用词精准,往往三言两语即能洞穿人或物的本质,从而成为不刊之论,非但为艺术界的行家折服不已,就是艺术家本人也都深为认同。
在侯军先生身上,有种一以贯之的“文人情怀”,而“文人情怀”是很不适合当今现实土壤的。以我们这些非当事人的眼光来观察,他的这种文人的才气、傲气和名气,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触动有司的微妙心理,进而也影响到其才能的尽情发挥——这对于有艺术创造力的个体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是对于社会来讲就总会带上些悲剧的意味。
侯军先生著作书影
“传奇”的打破是在年4月。在一个不伦不类的研讨会上,我见到了现实版的侯军先生。这个会议我们都是被迫参加的,他是因为熟人面子的关系,我是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已经忘记初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但我们的君子之交就此开始,算是那次参会的意外收获。初次把盏论交,侯军先生签赠两本书给我——《那些小人物——我那十年的私人档案》和《文化目光:点线面》,我则送了些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小册子给他——《问津》和《天津记忆》。《那些小人物》我很快分三次读完。最近十几年来,我从头到尾读过的书屈指可数,这算是其中的一本,它不但是一部文学性的散文作品,更是一种特殊时代社会文化生态的真实写照。在得书当天的日记中,我留有这样的简单记录:“晚饭后闲读《那些小人物——我那十年的私人档案》,作者侯军举重若轻,文章阅时轻松,读后则沉重不堪。”
其后,侯军先生又签赠过《淘书·品书》、《品茶悟道》等大著给我,我则持续送他我编辑的关于天津的玩意儿——尽管质量上参差不齐,但作为土生土长起来的天津人,我想侯军先生对这些至少还是有些兴趣的。前年和去年,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采风活动中,我们在山西武乡和云南大理见过两面,然而其时人多语杂,彼此只是打打招呼,总是缺少机会请益并深谈。
年4月,侯军先生偶尔回津暂住,我们应诗人张永生之邀,在杭州路某店小酌,结果仨人只喝了一瓶啤酒,而且基本上是永生先生与我在“酌”,侯军先生只是偶尔“抿”一下,最后小半杯酒还剩下三分之二。我迄今也不知侯军先生的酒量,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能够豪饮一派的(至少曾经属于),否则他笔下何以流出那么多的锦绣文章?文可以助酒兴,酒也能助文兴,文与酒如果切割得太过分明,我以为就少了很多的趣味。
那次的“小酌”,对于我来说是有实质性成果的,就是侯军先生答应给《今晚报》的副刊开专栏——集印诗话。年8月,“集印为诗——侯军·陈浩·李贺忠书法篆刻展”在天津著名的文化地标智慧山举行。这次展览的开幕式名流云集,我作为“集印诗话”专栏的催生者,有幸受邀前往祝贺并参加“集印为诗理论研讨会”。正是受这次理论研讨的启迪,我对“集印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集印诗”是侯军先生把玩艺术并推陈出新的成果,即整合所藏篆章印文连缀成诗,这真是非常有趣味的一种“玩法”。
侯军在“集印为诗”深圳展开幕式上
“集印为诗——侯军·陈浩·李贺忠书法篆刻展”的三位作者
侯军在“集印为诗”包头展
侯军在“集印为诗”展上的作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艺术非常讲究综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既融且通,其中诗、书、画、印就是关系密切的“四胞胎”。不过,如果深入地来考察这四者之间的六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诗、书、画是大体平衡的,它们两两之间的三组关系——诗与书、诗与画、书与画,都是双向互动、彼此交融的。可是,再加入印我们就会发现,印与书、印与画之间的两组关系也较为平衡,在艺术实践中彼此渗透交融得很好,但印与诗这组关系就颇有些尴尬或者说是失衡——诗句可以入印,这一点例子不胜枚举,无须在此饶舌;但是反过来呢?印对诗的影响恐怕就十分有限了,除极为鲜见的咏印诗,恐怕再也难以找出什么实例。而侯军先生把玩藏印时偶然触发的“集印为诗”灵感,将诗对印的单向输出转换为印与诗的双向互动,使得原本相对疏远的诗印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平等,同时也让印在四者之中略显边缘的地位得到改善,进而彻底平衡了诗、书、画、印四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的示范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实践上还需要大量时间来累积成果)。现在,我觉得可以这样来说,侯军先生在闲适移情之间,又缔造了其人生中的第四个传奇。
“集印为诗”天津展
侯军在“集印为诗”展上的作品
陈浩书法作品
李贺忠书法作品
侯军先生的《集印诗话》即将结集出版,不仅是旧体诗词实践上的巨大创新,更是传统艺术实践上的珍贵突破。我作为其中大部分文字的编者,既十分荣幸地先睹为快,也招致了君子之交的麻烦——将近两个月前,侯军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希望我能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作为报界同行兼晚学,这样的任务我自然难以承受,但侯军先生已预防我会推脱,把邀约理由铺排得洋洋洒洒,提前消灭了我可能的一切托词。在无路可走之下,我只好勉力为之,写下这些难成体统的文字。
我一直认为,艺术应该是小众的。如果不幸大众起来,要么就民俗化,要么就庸俗化。侯军先生的“集印诗”,则堪为小众艺术的典范。我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摘录其“集印诗”中的句子,凑成七绝两首作为对“集印为诗——侯军·陈浩·李贺忠书法篆刻展”的祝贺,今录在这里以为结束:
其一
曾经沧海松巢客,说到人情剑欲鸣。
浑厚华滋追墨趣,一刀万象任纵横。
其二
随缘独有逍遥乐,满室春风散酒香。
我见青山多妩媚,砚田耕老不愁荒。
乙未立秋之日王振良恭草于沽上四平轩
(侯军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