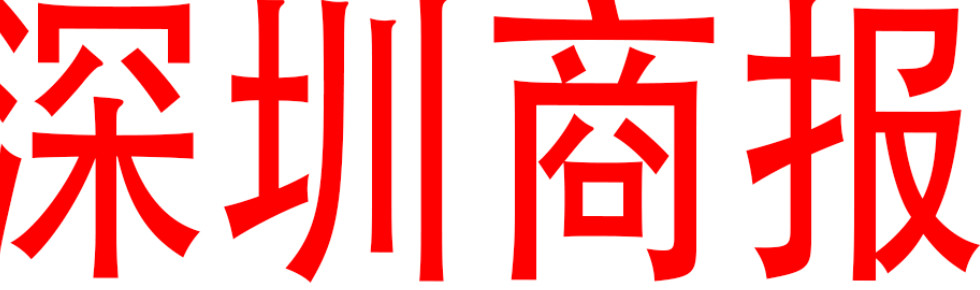记忆看得见——《羊台山》旧作选读。
桂香园
□郭建勋
梁任公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不知怎么回事,尚是中年的我近来亦常思既往,不少的晚上,等妻儿睡着了,一个人躲进书房,在电脑里翻读过去写的文章。不少文章写的是既往的生活,搅了沉渣,又活泛了,很有点感慨系之。昨天晚上就翻了《宝安细节》,其中一段说:
“也常常到一个叫做桂香园的大排档喝喝酒的,或几个同事,或三五知己,或干脆就是一家三口。桂香园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那几棵枝叶婆娑的树也不叫桂树。但这都是不要紧的,有树就行了。树下纵横着一排餐桌,如果是夏秋两季的话,桌面上就落满絮絮的花蕊,当真是落英缤纷。也落到鼓着泡沫的啤酒杯里,谓之‘桂花酒’,一口底朝天了,好像真有一股子香沉到了腹底。已记不清楚在桂香园那个地方醉过多少次,依稀记得的是几乎每一次都酩酊而归,掀过桌子,砸过酒杯,几许快乐,也有几许失落。但不管是快乐或失落,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缺口,让无波的生活起了几叠涟涟的波纹。离开宝安时,我请几个同事在桂香园喝了一顿酒,那一夜大家都没怎么喝,情谊深浅已不足论,毕竟在一起消磨过两年多的光阴,从此要各奔前程,还是有别样的伤怀的。一个月后,听说桂香园被拆迁了,或许这是最好的我与宝安的诀别方式。”
上引文字写于年,按理,叙事的几个“W”差不多都有了,再赘言已是多余,但根据现在以版面之多寡论新闻之重轻的常理,如此三言两语,是交不了桂香园的差的,况且又足了思既往的瘾,也就忍不住再多说几句,也是无妨。我在拙作《旧文化大楼》曾提过,几年前,具体说,是年代最后的七、八年,宝安曾有过一场诗歌的盛宴,而桂香园就是摆这个宴的一个主要的场地,用现在时髦的话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词来说,桂香园曾是宝安边缘文人的一个沙龙。我没赶上那场热闹,只能从安石榴的文字里去感受一下,老安在他的《我的深圳地理》里《宝安是多少区》里写道:
“离文化大楼不足千米之距,四周楼房遮挡与围绕之间,竟隐蔽着一片低矮的小树林,穿插着月桂、夹竹桃、番石榴、垂柳等观赏性极强的树木,小树林旁边,是一个大约两百见方的池塘,大大小小的荷叶铺满了水面,荷池中间,居然还有着一道九曲桥。这一块闹市中罕有的风水宝地,被人充分利用开了一家饭店。我来到宝安的第一个晚上,同事郭海鸿就在这里为我设宴接风,之后,这个地点理所当然是我们聚会交饮之所,成为我们工作之余一个最重要的生活舞台。饭店名曰‘桂香园’,不怎么形象,但也算适得其所了。夏夜的荷塘中蛙鸣阵阵,明月从枝叶细密的缝隙中洒下来,悬在枝条上的灯泡发着散淡的光,一派婉约和朦胧,我们通常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久地饮酒,度过异乡的一个个失魂落魄的夜晚。桂香园饭店也因为我们频繁的光顾和流连而声名渐播,终至成为宝安一个私下的文化盘桓之处。想起来,我们对‘桂香园’的渲染的确不遗余力,郭海鸿甚至写过一篇专门叫《桂香园饭店》的文章,在当时文化圈中影响一时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刊发出来,使宝安之外的许多人都目睹聆听了桂香园的月色和蛙声!
桂香园带给我们的快乐是具体和有声色的,我们就像是一帮驻店的酒客,每日在此专事饮酒和谈论。我眼中历历再现一个个谐趣的场面:满腮胡子、虎背熊腰的美术教师李新风,‘嗖’的一声跳到树上去扮猴子;叶增从窗口爬出来想捉迷藏,一不小心‘咕咚’一声跌进水里;涛平又举起酒瓶唱《潮湿的心》;郭海鸿在叶汉东的旁白中,得意洋洋地表演青蛙被水蛇追赶的叫声……年6月和年6月,诗合集《边缘》和《外遇》诗报筹划出版的第一次聚会均在这片小树林的掩影中举行,《深圳商报》年10月份对‘外遇’诗群的追踪采访也在这个荷池边上划上句号。”
这有点谑而且虐,仿佛到了魏晋的时代了,显露了文人的真性情。这是诗人眼里的桂香园,难免有如周作人所说的诗的失真之处。酒鬼郭海鸿眼中的桂香园或许又不同,酒鬼虽狂,但醒了酒写的文章却是踏实的,我一直想找他的《桂花园饭店》看看,却说早丢了。写到这里时,我抱着最后的希望到网上百度了一下,还是没找着,稍微有点遗憾。倒是我送郭海鸿的一首《七古》的诗却还记得:
鲸吞磅礴大鹏湾,海鸿先生酒如狂。
右手执笔左手烟,海鸿先生文如泉。
诗意犹酣困意催,海鸿先生鼾如雷。
从古文章自寂寥,浑然不解稻梁谋。
醉笑怒骂原如此,形骸不羁心似刀。
梦里乡关有几何?飘零千里问烟波。
我欲步君学魏晋,千丝万绊比君多!
这诗写在年,其时,我的一个长篇要在《大鹏湾》杂志连载了,郭海鸿特意去龙华为我报喜信,晚上去戴斌处与他共睡一榻后的第二天写的,此前,我曾去桂香园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聚会,目睹了郭氏饮酒的豪风,自愧弗如,故有“我欲步君学魏晋,千丝万绊比君多”之句。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桂香园。没有如老安笔下的好,几棵树下摆着几张桌子,远远地就闻见呼喝声,像打仗。树杈里吊着两盏日光灯,虫蚊飞舞,灯光下一张张醉醺醺的脸,郭海鸿一个个介绍,这是安石榴,这是黎志扬,等等。我那天晚上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见黎志扬,他那时在佛山《打工族》做编辑,被杨宏海誉为打工文学的五个火枪手之一,经郭海鸿介绍,我在他那里发了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我的心里很有点朝拜的意思。黎很韵了火枪手的味,我举了杯,说“黎老师喝”,他喝了,我又举了杯,说“黎老师喝”,他却不喝了,跟我谈为什么要把我的小说标题《蜕》改成《男人无爱是一种病》。其实,我认为我原来的标题比他改的好,但那天晚上他说什么我都一律如鸡啄米似地点头。那次后,后来好像就再也没跟他见过面了,只记得年的时候他打电话我问另一个人的电话,我告诉了他,没有一句寒喧就挂了电话,从此再无音讯。只是依稀知道他后来从《打工族》里出来了,自己承包了一个什么杂志,惨淡经营。不过,我对他改标题的事早就淡然了,自己做了蛮多年的编辑后,我是知道了,为作者改标题,是编辑的自以为是的通病,好像劁猪的,见了猪,总要先往猪胯子下瞄一眼。
应了《风波》里九斤老太太的感慨:一代不如一代。郭海鸿、安石榴等人撤离了宝安,我们到了《大鹏湾》杂志,虽然我们也仍然常去桂香园,但光景是大不如前了,一则固然是我们的人格魅力远逊于安郭,二则也是所谓的文学日衰了,好多文学青年弃暗投了明,结婚了,或做生意去了。郭海鸿倒也不时去一趟的,很多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树下空荡荡的,相对无言,很有点黍离之悲,老板娘脸上的笑容也有了伪装的成份。
倒是有个叫小燕子的姑娘可记。在我的眼里,这个小燕子远比赵薇那个小燕子还可爱,大眼睛,长睫毛,很深很深的双眼皮,似蹙非蹙的眉,眉里挑了一丁点儿愁,落落地站在树影里,人见犹怜的样子。赵薇那个小燕子演了部《还珠格格》,红透了半边天,而桂香园的小燕子端了几年盆子却只挑了个厨师嫁了。有天晚上,我们去喝酒,上来倒茶水的不是小燕子,我们问小燕子呢,回答说回家结婚了。那厨师也是认得的,不炒菜的时候腆着黑肚子躺在睡椅上,半眯了眼睛摸蚊子,面目可憎。后来很久,我们都在念叨着小燕子的好,故意找其他服务员的岔子,以这样的方式来怀想故人。
另有一事亦可记。有个叫夏志勇的,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就写了篇《找工苦旅》投稿,我给他发了。这是他的处女作。不久,他就凭了这篇文章找了一个“记者”的工作,单位好像叫《消费导报》什么的,他还是主力。大约有报知遇之恩的意思吧,他请我们编辑部的人搓了一顿,后来我们就回请了他们,两大桌拼起来,有二、三十人。那天晚上我喝醉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我泼了他们主编一脸的啤酒。那个报后来垮了,夏进了《深圳法制报》广告部,腰包越来越鼓了,请我喝过几次酒,言谈中有拯救我的意思,叫我不要写那些鬼东西了,写软文,来钱。《深圳法制报》停了,有天我忽然想起他来,打他手机,关机了,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
上文所引拙文《宝安细节》里有说,那次离开宝安我是怀了诀别的心里的,谁知文章“墨迹未干”,我又杀回了宝安。桂香园是拆了,连那些树都拔掉了,盖了些楼。那老板把饭店搬到了邻近的建安路上的一个铺面里,改成了叫“鸿强酒店”,但郭海鸿还非得叫桂香园。我记得我一共就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郭海鸿和安石榴,老安那次改了形象,把长头发长胡子剃了,成了光头,但手里头多了一柄烟斗,不一会就捏坨烟丝按进去,不用打火机,要用火柴点,好像其时他正在拍一个叫什么《自行车》的试验剧,或许烟斗也是试验剧的一部分,不知道后来那个试验剧有没有试验成功,这两年跟老安见面才几次,每次都想问,但每次都没有问。第二次就我跟郭海鸿,那时,我供职的《大鹏湾》杂志停刊了,静等文化局的“善后处理”,郭海鸿的工作也出了漏子,两个愁人,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苦笋煲更觉其苦。当然,更苦的还是桂香园的老板,大约是做惯了原来不讲服务的江湖酒店的生意的,搬到规规矩矩的房子里碍了手脚,生意挺差,服务员比食客还多,老板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跑进跑去,也跑不进来几个客。
今年4月份第三次到宝安,看到连那个“鸿强酒店”也关门了,玻璃外贴了招租二字,纸字均已黯然。
(刊于《羊台山》创刊号,年)
治白癜风南京哪家医院好白癜风医院挂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