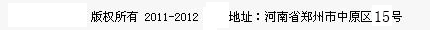点击上方"同步悦读"免费订阅
觥筹轶事■陈世魁
年早春,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其时我已经有些酒量,却一直难养酒瘾,所以觥筹之事便也时有时无。就在那时有之中,衍生出惺惺相惜的友情和外人难解的轶事。
同时留校的,有位叫束因立的仁兄,是位已淮北化了的上海人,有着一副让人嫉妒的英俊的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一双深邃的明眸不容丝毫杂质,清澈明朗,透着聪颖练达。他的性格,语言,为人,处事,与淮北人几无差异;然其学养、气质、言谈出卖了他,实在是掩饰不住此君绝非淮北人的本来。
那些年,我和束君等常周末小聚,有街头食摊灯下小酌,也有居家放量豪饮。除我和束君外,还有孟二冬、李宁二君,也是我们一届留校的。那时酒一两元一斤,大都是当地所产,地地道道粮食酒,醇香清冽,绝无酒精勾兑之虞。有时也会奢侈一下,喝古井贡、口子窖,便感阔绰的不知自己是何等人物。我们喝酒有个约定:在街头小摊绝不猜拳行令,只有在各自舍下方可老虎杠子鸡。喝酒之初,我们还都君子雅士,一盅盅连碰几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逸闻趣事,说的都是陈年旧事,且大多是他们当“知青”时的事。我没有下乡插队的经历,当然难接上话插上嘴。随着酒肉穿肠的进程,束君便开始充当发言人一一不是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是有问有答的,他却不。我们虽没被忽略,也只剩了一个表情包的功能,多是附和着“嗯”“噢”表示没偷懒、也在说、没闲着。有束君在,轮不到我插话,他是话语权的拥有者,而且,不光是我,谁他妈都说不成,至少说不完整。偶尔插话胆敢超过2秒,立即会被他毫不留情地压制,没有一点民主精神。说羡慕嫉妒恨,极端了一点,说酸溜溜的肯定是少不了的。
但那酒喝的,却很民主、很公平,货真价实的各行其事,一般每次都会消灭2斤壶中物,至于谁多谁少,从来就是一笔糊涂帐,再有能耐的高手都别想理清个应借应贷。束君豪爽,说话音量和他讲课一样大可震耳。束君教学功底深厚,效果绝佳,课堂上经常博得学生的掌声,实属罕见。此君热力四射,为人坦荡,普罗大众无不明爱。二冬属学者型人物,留校之初,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名声大振。此君喝酒与做学问一样,做多说少,沉默寡言,然酒量却豪放,不容小觑,基本是一饮而尽,和他没有酒官司打。李宁也是上海“知青”,个头不高,相貌清秀,小家珍玩,内敛可人,说话小声小气,且酒量在七般八般之列,然偶尔也有不请自斟的壮举,且会很淮北地来一句“我剋一个”,此时便觉得此君也颇有梁山之魄。
束君喝酒,酒如其人:干净利落,豪爽透明,淋漓酣畅,清澈见底。和他小酌,你不用劝他,他不会逼你。毫不夸张地说,酒者皆有君子之风,喝者自喝,停者自停,你喝没谁拦你,你停没人劝你,与自斟自饮别无二致,我自觉这才是朋友哥们。
束君喝酒有个特点,酒至五六分时他会哭,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泪流不止的哭,难以劝止的哭。不说每次,也是经常。但他从不解释就里,哭完继续喝,且仍谈笑风生。次数一多,我等便习以为常,以为只是习性而已。
终有一日,在一个与其独处的环境里,束君道出缘由:束君的父亲是上海的著名作家、资深老报人、《新民晚报》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辞海》副主
编束韧秋先生。“文革”中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多年,下放改造,批判反省,历经磨难,不久前终获平反昭雪,恢复工作。想起那些起起伏伏的过往,难免悲感交集,遇到合适场合,合适对象,久滞于心的压抑,情不自禁地释放……关于他父亲的名人身份,他从不丝毫示人;对他父亲所遭遇的不公,他也守口如瓶。在校学习期间,很少人知道他的家世有那么大的吓人的头衔,由此,我对他便更加尊崇。
时过境迁,光阴飞逝。几位后来陆续离开学院:先是孟二冬考上北大硕士、博士,李宁调回上海在一个中学任教,束君调到《深圳商报》社做了编辑,只有我在固守旧地,于是酒事渐少,直至消失……
延伸阅读——征稿:全民阅读书香中国《军绿》面向全国征稿关于“同步”年终盘点:纸媒发表一览年终盘点:我最满意的作品年终盘点: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一览年终盘点: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一览(关于微刊)在这一千八百多个日子里关于写作和投稿的几点建议特别